 |
八十岁了。伊斯梅尔·卡达莱。史上阿尔巴尼亚出的知名人士为数寥寥,内有一个位置属于他。粗通世界地理政区之人,一般指认不出阿尔巴尼亚的位置,能指认的,也未必叫得上来除首都地拉那外第二个城市。在卡达莱的书里,你至少能看见“吉诺卡斯特”这个地名,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时间,是1936年1月28日。
我找到《巴黎评论》著名的作家访谈系列里卡达莱的一篇。搁在别人,话题一下子就深入到访谈对象的某部作品,或做过的某件事、持有某个观点上去了,轮到卡达莱,他得先普及一番ABC:
“阿尔巴尼亚文学基本上源于口头。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本文学著作出版于16世纪,是圣经译本。当时,它是个天主教国家。自那以后就有作家了。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奠基之父是19世纪作家纳伊姆·弗拉谢利。虽然不像但丁或莎士比亚那么伟大,他仍然是创始人,是标志性人物。他写长篇史诗,也写抒情诗,唤醒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意识。在他之后是杰尔基·菲许塔。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人是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巨人,孩子们在学校里都要读他们的书。之后出现的别的诗人和作家,作品可能更好,但他们不能在民族记忆里占据同样的位置。”
这些常识,到祖国之外的每个地方,他都得播讲一番。
阿尔巴尼亚跟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与人们略更熟悉其文学的其他东欧国家,比如捷克和匈牙利,也都不具可比性。这是个偏种姓化的国家,压抑,落后,直到1913年才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来又依附意大利,成为墨索里尼进击巴尔干的入口。在卡达莱7岁那年,德国人又来了,两年以后尘埃落定,它被转交给苏联。
最早是一位自封的国王(佐古一世)独揽大权,战后,党派和宗族把持着阿国的命运,它一方面抗拒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苏联集团强压下来的斯大林主义,对他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充其量,也就是证明该国是苏联集团里的一个“合法成员”。接下去,关于阿尔巴尼亚,所有的新闻就都绕不开它唯一的强人——恩维尔·霍查了。
在一个如此小、如此边缘化的文化和语种里,卡达莱本来是有机会也有理由离开的。卡达莱小说的中译本,尤其是最近半年里出版的《三孔桥》、《金字塔》、《雨鼓》、《耻辱龛》等等都系法语转译,是因为卡达莱同法国的关系密切,他的第一部小说《亡军的将领》,就是通过法译本在法国打响了国际名气。他留在国内,跟一个在外族强权和本国独裁者的连续统治下,好不容易寻觅到自我身份的文化待在一起,坚持写了逾五十年的小说和诗歌,称得上是劳苦功高了。在国内,他被霍查所庇护,又能写出一些明显讽刺时政的小说,此人的精明、识时务、善于自保,同他的才华也是不相上下。
《亡军的将领》也是我读的第一本卡达莱,至今犹记当时的震撼。二战结束,一个意大利军官受命前往阿尔巴尼亚,去给死在那里的士兵收尸安葬。收尸可不是简单的打扫战场,清理遗物,亡灵飘荡的土地肯定是不同一般的,被迫接触他们的活人,自己的灵魂也一定会被改变。它是1962年,卡达莱从莫斯科的高尔基学院进修回来后完成的作品,此时霍查已经领着阿尔巴尼亚人走上一条背离苏联的道路。八年之后,小说的法译本轰动法国,卡达莱本人也被请去了巴黎,对于铁幕意识浓重的西方人来说,这样一部具有人性关怀的小说,可以证明在他们眼里一片荒瘠的东欧文化人集团,出现了一个有分量的人物。
读卡达莱的作品,总会想到他在“西方趣味”和“本土主义”之间采取的位置。《亡军的将领》写意大利人的事,以贫瘠弱小的阿尔巴尼亚作背景,让法国人读得拍手叫好,这样一个创作—接受圈的形成,也得靠“因缘际会”。卡达莱最幸运的地方,就是在国内,他的写作只需对霍查负责,而霍查其人,跟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那些拘谨、严厉、乏味的领导人不同,早就对西方芳心暗许,尤其是,霍查跟法国有一段不解之缘,他脸上不仅有红色东欧领导人典型的外表特征——城府,还有一股难以让人忽略的纨绔气质。
即便只是为了跟西方人表个态度,他也要给卡达莱以包容。于是就有了后者1973年的“触线”之作《冬日的伟大孤独》,它以一位东欧独裁者为主角,描写他的志向和挫折:他诚笃、豪爽,胸有抱负,想要率领人民脱离苏联集团,他祈望得到中国的奥援,畅想着让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轨道,同西方世界自由往来。但在现实面前,他一再受挫,许多良好的愿望都结出了恶果。这是一部立场含混的作品,既有美化独裁者人格的一面,又有批评他的一面。卡达莱投石问路,想看看他究竟能得到多大的自由,人们很难说他阿谀奉上,因为他描绘的只是一个领导人理想中的样子。
试探让他付出了代价。虽然霍查本人保持沉默,但以霍查夫人为首的一群斯大林主义老左派,根本不考虑小说中的婉曲之义,直接把此书打为“诋毁领袖”。卡达莱受到了一点完全可以接受的处分——他被逐出首都,流放到阿尔巴尼亚中部地区。后来,他又因为《梦宫》一书遭到一些“迫害”。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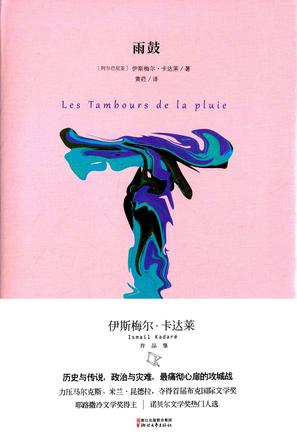 |
卡达莱部分作品的中译本
站在1991年之后的立场上回看,这些受难都是他的资本,不过,这些代价相对而言都是很轻的,卡达莱一直就是官方和民间两边均认可的人,一大原因在于,除了《冬日的伟大孤独》(出版时因忌讳“孤独”而改为《伟大的冬天》)、《梦宫》、《错宴》这种涉及现实政治的小说外,他把大把精力都放在写历史小说上。卡达莱是历史专业出身,写作技法高妙,他能把极其荒诞的政治现象写得有如发生在另一个国度的寓言,削弱故事的刺激性,让一些保守分子难以抓把柄;而他的历史小说,如《雨鼓》、《三孔桥》、《耻辱龛》、《破碎的四月》,写的多是发生在奥斯曼甚至更早时期的事,其中的自然景观,社会风情,包括人物姓名和习性,却又让今天的人读来感觉熟悉。
在《雨鼓》里,我们看到阿尔巴尼亚是一片多石的崎岖之地,15世纪的一天,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浩浩荡荡开来,围攻一座孤零零的阿尔巴尼亚要塞;《三孔桥》,写一条本来只有摆渡船的河,一些神秘人物私自与地主们达成交易,造起一座桥,河边不明内情的居民们仿佛看见了某种宿命正在发生,河神在暴怒,空中风传着土耳其人进犯的消息;《破碎的四月》写19世纪的事,北方高原民间通行的一部“卡努法典”,在数千户山民之间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仇杀游戏;《金字塔》则干脆把时间轴挪到了埃及法老胡夫的年代,他遵从祖训,下令建造金字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像《亡军的将领》里那位意大利军官一样,感觉到亡灵的召唤,分不清自己是死是活。
在高尔基学院,卡达莱接受了苏联官方指导的作家训练,未来的红色作家都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格式来打造的,必须写现实,提炼积极的、有益于人民凝聚的东西,从现实通往畅想中的未来,只有唯一一条上升的道路。然而,卡达莱形成的个人风格却可以恰切地称作“梦魇现实主义”,他的小说的主角不论要去完成一件怎样的事,都会预感到自己在未来某一时间点上的命运,它早已被安排好,所有的努力,一切挣扎,都是在往那个时间点逼近。这预感总是突如其来,如同借了一对噩梦的翅膀。
法老胡夫,意大利将军,都觉得自己虽生犹死;《雨鼓》中的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早早就得到了丧师覆军的预兆;《错宴》写1952—1953年苏联发动的“医生阴谋”,一个阿尔巴尼亚医生被诬陷入狱,他为自己的辩白里已隐含着认命;《破碎的四月》里,一上来就杀了人的乔戈,之后一直在等待一颗杀死他的子弹。
这颗子弹终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飞出。读到《破碎的四月》的结尾,我被一种强烈的快感所击中。人终于与他的宿命相拥了,而相拥的时刻往往安静而肃穆。在《雨鼓》的故事进入尾声,奥斯曼军队战败退军,将军在中途平静地吞下了毒药,之前一直盼着侵略者一败涂地的读者,此刻也该沉思了。哪个人的生命不是在把一丈白绫扔向自己的神明?不同的只是有的生命没有被书写,有的生命被书写出来,而成为可以传诵的悲剧。
卡达莱落笔有凛冽的朔风,他特别善于写肃杀的氛围,在那些古老或不太古老的时代,人们尚没有萌发自我意识,抬头三尺就是神明在游荡。读他的小说,有时就像读旧约圣经一样,感到马上就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卡达莱描写的景观,如同印象派绘画,都是个人感受的产物,这种感受往往是压抑的:他在自传体小说《石头城纪事》里写他的吉诺卡斯特,那个遍地都是石制古屋的城市,从街道、喷泉到石屋屋顶,都覆盖着有如巨大的鳞片的灰色石板,“很难想象,在这些厚重的硬壳下面能有柔软的生命存活并繁衍后代。”在苏联求学时,他说克里姆林宫有着“蹲伏的砖墙”,他对这景观的感受,尽在不言中。
“老人治国”模式拖垮了东欧诸政权,“老人”不仅指年龄,还指停滞不前的心。恩维尔·霍查,正如卡达莱在《伟大的冬天》里所写的那位独裁者,一腔豪情落了空:苏联被他甩掉,而他所倾心的中国根本不理他,自己倒是热热乎乎地去迎接尼克松来访了。西方人宁认卡达莱,不认阿尔巴尼亚,因为在他们看来,卡达莱应该是东欧的一个绝对异类,应该是独裁者们的眼中钉才对。几次重挫之后,孤独之中的霍查,也变得像当初的斯大林一样,总在疑心有人要阴谋颠覆他;他不停升级对社会的管控,到了末年,霍查同志几乎就是一个小号的勃列日涅夫。
是运,但也是命。卡达莱对霍查肯定有同情,两人的气质长相都格外相似。他所写的领导人,除了《伟大的冬天》这种一目了然的指涉,像《雨鼓》中的奥斯曼将军身上,似乎也能看到霍查的影子,一个处在灰色地带的复杂人物,时而大发淫威,时而敢做敢当,顺利时踌躇满志,遇挫时悲伤得就像一个被反锁在房间里的孩子。对卡达莱来说,意识到命运的人总是能有一些英雄的时刻的,因为他们心中有了恐惧。
《亡军的将领》、《雨鼓》、《破碎的四月》,这些都是卡达莱的杰作,最有史诗气息,“史诗”二字并不可怕,哪个层级的读者都能比较轻松地进入到他所构建的世界里。八十岁的卡达莱,已经得到了分量极重的布克国际文学奖,年轻时一本本写书,老来拿奖拿到手软,也是一个逃不了的宿命。他的另一个宿命,是必须不时地被人问起与霍查说不清的关系。这些人真是不知足啊!卡达莱说,又希望我爆料,又责备我怎么没有去做烈士。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