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张洪平
前不久,北京限制外地牌照的政策再次收紧,这被不少崇尚自由主义的社会与经济学者猛烈抨击,北京交管新规再次成了政府行为扭曲市场经济的佐证。在各地掀起“抢人大战”的当下,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在拒绝人口的流入,难免引发广泛的质疑。北京究竟有什么底气敢“逆历史潮流而动”?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城市化”与“逆城市化”是怎样交锋的,未来哪派力量能够占上风。
事情的起因是,6月15日,北京市交通委、环保局和交通管理局三部门发布通告,对外地车牌载客汽车的限行范围扩大至六环内,同时每辆车每年最多办理进京通行证12次,每次有效期最长7天。从2019年11月1日起实施。
新规出台之后,几家欢喜几家愁。没摇到号暂时挂外地牌照的车主们愤愤不平,已经有了北京号牌和更多没车但嫌弃道路太堵的市民则拍手叫好。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体现得淋漓尽致。

客观一点地说,限制外地号牌车辆是所有一线城市的普遍做法,这既是城市管理者应对“大城市病”的无奈之举,当然也难逃反对者们对当局“一限了之”“懒政”的攻讦。
从微观上看,人口向城市聚集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会受到各种条件的约束。
从经济角度看,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不可避免。人为地增加人口进入一线城市的成本,限制了“人”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了潜在的生产率提升。而一些客观上的限制,如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其实也都有技术上经济上的解决方法,这已经被无数学者从各个角度论证过了。

从政治角度看,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也有很大阻力。人口大量涌入会增加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降低城市的宜居程度,而且城市要不断地增加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间,肯定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比如“新市民”与“老市民”之间的冲突,甚至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而且地方政府在资金、资源、人员上的增加往往落后于现实情况的变化,这也激化了矛盾。此外上级政府还要考虑地区间的发展差异问题,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也使得政府在“人口自由流动”的问题上多了一层顾虑。
如果从宏观上看,国家也不能无条件地“放任”人口向东部大城市迁徙。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如果完全没有行政上的调控,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那么中国整体的人口分布应该是符合经济总量分布的,人要往高处走,向机会多能赚钱的地方迁移。我国整体经济是东部好于西部,南方优于北方。所以自由条件下,大部分人口会向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集中。
而且这种趋势符合马太效应,人口越聚集,劳动分工越细化,生产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对人口越有吸引力,它会自我正向循环不断强化。最终的人口分布很可能比“二八定律”还要极端,一两个省占全国经济总量的80-90%都有可能,人口5000万甚至过亿的超大型城市(群)也不是不可能。

但在经济效率提升的同时,在这些城市受“大城市病”之苦以外,从全国角度看,人口过度向少数城市和地区聚集还有其他坏处。
从国家安全角度,要长治久安地治理一个地区,人口的数量(密度)是基础,要实现对土地的有效控制,首先必须有充足的人口。地广人稀的地方向来是“易攻难守”的,或者成本极高。俄国向美国出售阿拉斯加,法国向美国出售路易斯安纳,并不是冲那几个小钱去的。而是他们知道,要真正统治这些地区不仅代价极高经济上不划算,而且随着美国实力的扩张,就凭自己那几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要保住千里之外的“飞地”,成本太高难以承受。所以与其打一场没胜算的战争,然后割地赔款,还不如趁早卖掉。
人口对边疆地区的地缘战略安全尤其重要。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独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苏联执行的政策,使少数民族集中在边疆共和国,当地俄罗斯族(斯拉夫-高加索人)比例偏低,一般不超过20%。所以在苏联对边疆地区控制力下降后很快独立了,原本的“少数民族”成了新国家的主体民族,俄罗斯族反倒成了少数民族。

这对中国很有启示,我们也不能放任边缘省份人口过少、民族单一化,因为一旦有事,很容易产生分裂主义倾向。姑且不论泛突厥化思想的影响,光是境外反华势力的煽动就让人防不胜防。对此,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
那怎么让人口愿意留在当地呢?难道靠“多生”吗?不过即使再怎么“多生”,只要大城市的吸引力不减,那人口流出的趋势就难以逆转。比如各地接连出现的城市间“抢人大战”、对“人口红利”消失的焦虑、对“未富先老”的恐惧,还有社保基金全国范围“调剂”的相关新闻,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现在确实已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像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点,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快速进入老龄化、甚至是超老龄化社会,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民生问题,还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这需要我们的领导人拿出一套整体的综合方案,才能让中国这艘“大船”稳定住,并且继续前进。

要解决人口过度向大城市聚集,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没有吸引力的问题,其实关键是解决“公平”的问题。古今中外,公平问题是限制人类进步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原动力之一。比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演变到今天的高考制度,要实现全国范围内大家都遵守你这套体系,那你一定要是一个能“服众”的制度。最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就是按地域给定名额,然后在同一地域内按成绩择优录取。这样无论你的初始条件如何,都是在和身边的人竞争,寒门子弟也有希望,社会流动性不枯竭,人心才能稳定。
西方也有类似的以“公平”为目的的制度设计,比如陪审员制度。陪审员制度的目的,不是为了公正,也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服众,为了“公平的表象”。你想象一下,在公民中随机抽签决定若干名陪审员,他们除了和控辩双方没有利益冲突的共同点外,其实来自各行各业,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法律的理解也是一知半解,他们难道能做出比专业法官更公正的判决吗?当然不能,庭审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控辩双方律师煽动陪审员情绪的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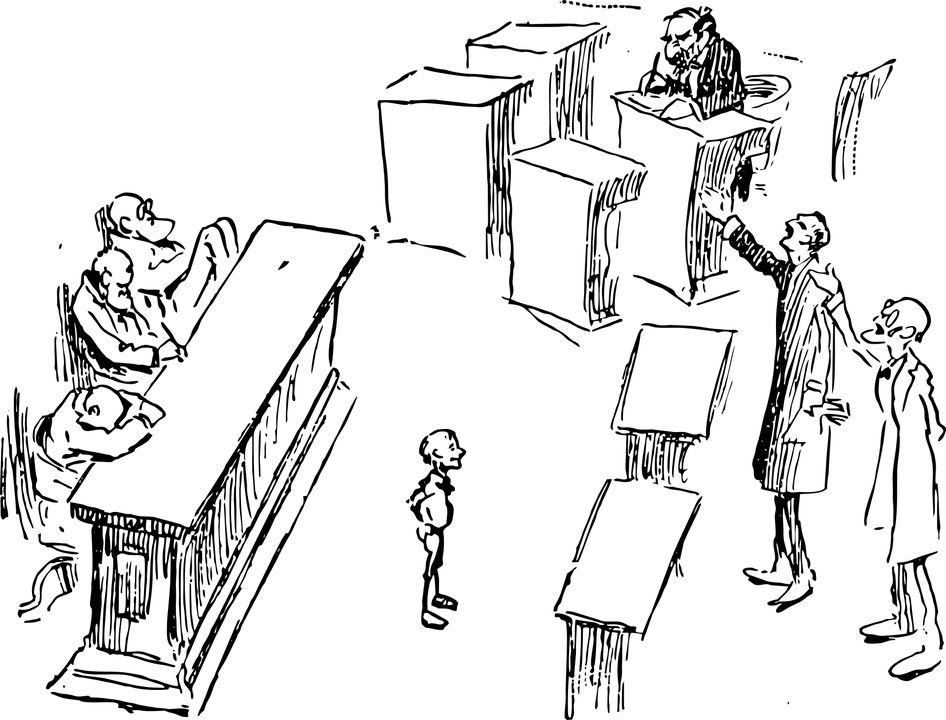
那么为什么还要选择这种制度呢?关键就是为了制造一个貌似“公平的表象”。实际上即使在发达国家,最终进入陪审员出席的庭审阶段的案件也是少数。以案情影响力最广的刑事案件为例,很多案件都在开庭前,嫌疑人就选择和检控方达成认罪协议换取轻判,这样既达到了惩治罪犯的目的,也节省了审理案件的社会资源,是人类“实用主义”的一种智慧成果。
而真正耗到要开庭审理的时候,审判的目的就变了。嫌疑人是否真的有罪,罪罚是否相适应,这些都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让法庭内外的人都相信,罪犯会受到正义的制裁,善良的好人会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信任让社会全员能在未来继续保持合作的关系,相信破坏规则的人会受到惩罚,这是法院判决的真正意义。而陪审员制度就是在表明,审判是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这种行为是民众的决定,所以必然是“公平”的,必然应该得到大众的支持。
我们在国家层面上探讨人口政策时,也不能忘了这个政策只有在大众认为你是合理的,认为你是公平的时候,政策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否则当人人都不服这个法律,在无时不刻千方百计地找漏洞时,你这个法律也就失去了意义。“法不责众”不是因为人民太刁蛮,而是因为法律本身制定的就有问题。

具体来说,怎样的政策和法律能让大家感觉公平呢?怎样才能吸引一部分人口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呢?公平此时体现为一种平衡,一种自由选择不同结果的机会。
国家层面的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手段。比如东部、南部经济更发达,但生活成本更高,同时政府可以从经济生活中征收更多(但不一定是更高比例)的税收,而这些税收不能都用在本地,而是要从国家层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就像人口流入地的社保基金更充沛,但你不能全用在本地,而是要向这些人口的流出地,生养了他们的地方进行补偿,补偿他们的父辈祖辈。此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也是中央手里的工具,多种手段组合使用能实现“1+1>2”的效果。
中部地区怎么办?他们既没有大城市的先天优势,也难以争取更高额度的中央补贴,处于两头不靠的尴尬状态。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部分人选择离开,到机会更多的地方去拼搏,剩下一部分人利用当地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本来收入不高,但因为走了一批人,他们面对的竞争少了,所以收入有所回升,尽管可能比不上离开的人,但也能维持下去。

这公平吗?也许不同立场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但在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之下,这种安排就是最优的。国家要为全民提供公共服务,如卫生和国防。这笔账没法清晰地算到每个人头上,你要么接受这笔“糊涂账”,要么去别的国家接受他们的“糊涂账”。人生就是选择和权衡。
人们要的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公平,而是现实要处在心理上相对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要么我去大城市,承受更大的压力,忍受更恶劣的环境,同时赚更多钱提升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要么我去小城市或者农村或者困难地区,压力小一点,自然环境好一点,但较少的薪酬加上一点国家补贴的福利也比不过大城市。
如何抉择?如何取舍?这是个人的问题,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不能也没法干涉。我们只需要知道,只要你给出了政策上的倾斜,现实就会朝你干预的方向拨过来一点。一切选择都有代价,自由放任也是一种选择,而且未必是在长时段里对国家整体最好的。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把行政管理从粗犷向精细进行转型,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维持平衡。一刀切的限制不好,完全放任自流也有问题,现实的最优解应该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即“有调控的自由”。而且这种最优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代和环境需要不断微调的。整个过程难以一蹴而就,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解释了大城市集聚人口的利弊得失,分析了从国家整体角度难以放任人口自由流动的难处。最后给出了解决方案:国家层面的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手段,用转移支付和产业政策等手段,实现“有调控的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在结果上还能体现公平原则,最终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维持平衡,让中国这艘“大船”平稳地继续前行。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