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比尔·布莱森的科普名作《万物简史》,发现19世纪真是奇人辈出,时不时冒出一个独立研究者,做千奇百怪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却因种种原因不愿发表,或发表了也没人搭理,又或与别人争执一个发现的独占权不下,一赌气就此退出科学江湖,诸如此类,有趣得很。我们看以前的人,总以为他们特在乎自己理论的正确与否,在那上面押了一世英名,其实未必,那时的很多理论其实只是一个解释模式,一个想象的产物。比如托勒密,能以科学手段证实地心说,他觉得很开心;19世纪那些人也是,科学在他们眼里首先意味着想象力,集中火力去证明一个构想,哪怕它荒谬绝伦,也是乐莫大焉。
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成了多数人的科学常识,在1859年刚刚提出时也只是个构想,并没有足够的化石证据,就连达尔文本人,也曾被这一想法之奇异而震撼,发表《物种起源》前,他还犹豫过很久。但他的脑洞在家族里还不算最大的,他还有个小两岁的姑表弟,正当英国人交头接耳地热议达尔文之际,他一个人在英伦诸城镇里游荡,两手插在口袋里,观察路上的每一个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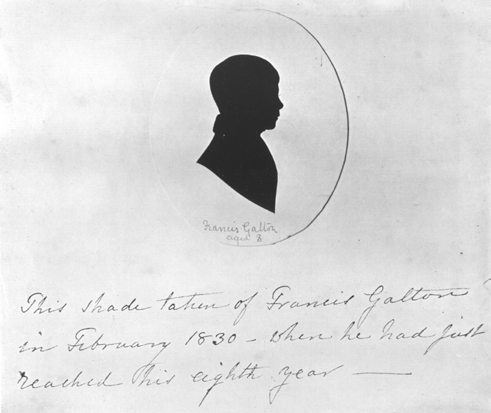 |
8岁的迦尔顿 图片来源:https://www.galton.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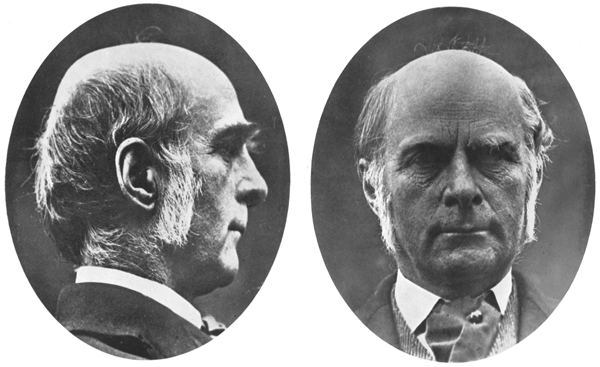 |
迦尔顿标准像 图片来源:https://www.galton.org/
弗朗西斯·迦尔顿,与托勒密一样,也有计算和测量癖。他活了将近90岁,这个寿命足够他去做很多奇怪的计算,例如,他研究过需要多少笔才能画成一幅油画,他给一壶口味完美的茶设定了一些参数,他还研究过祈祷对人的好处,结果显示,牧师的寿命并不明显比其他职业的人长,具体能活多久,可能跟他们祈祷的内容有关。
最离奇的是他观察女人的方法:他把一张纸撕成小块,塞进一支耶稣受难十字架的凹槽里,又把一根针镶在顶针上,戴着它,攥着十字架放在兜里。看到路过的女人,比如一个他认为极有魅力的女人,就悄悄地在塞在十字架顶端的纸片里戳个洞眼,看到一个“中人之姿”,就在十字架横木的纸片里戳个洞眼,下面的长端部分,自然就用来记录他眼里的丑女了。
你觉得滑稽可笑,他可不这么认为,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行为体面是大事,迦尔顿要是掏出个本子,美女、凡女、丑女各画一栏,在里面写正字,被人看见,那可太丢家族的脸了,灵魂都要受到谴责。他的观察行为要彻底神不知鬼不觉,一面还手摸十字架,纾缓良心负担。他根据统计结果画了一张地图,声称,伦敦的年轻女子全英最美,而阿伯丁的女人全英最丑。
统计这些究竟有什么用?不要想歪了,迦尔顿爵士家境富裕,自幼聪颖,长大了也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考察了猪马牛羊的择优育种,迦尔顿灵机一动:人类不可以改良吗?应该在英国人中选出最有修养、最聪明、繁殖力最强的人来提高整个民族的质量,他说,很久很久以前,英国就有这样的传统,长矛骑兵参加比武赛,最终胜出者可以赢得最美的妇人……这太美妙了,如果让拥有最完美的素质,道德、智力和身体都达到最佳的人婚配,我们种族会是什么样子?
嗯,政治不正确的气味出来了。好在我们可以理性地鉴别出其中的时代特色。那是个比较乐观的年代,“种族”后边还没有可怕地带上“主义”二字,很多受到进化论影响的科研人员觉得,人类理应通过进化变得更好,而我们可以为此做点什么。迦尔顿耗费在测量上的精力不亚于今天的任何搞田野考察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他观测美女的目的也那么光明正大。在回忆录中,迦尔顿坦言这项研究是纯个人的,但也堂堂正正地自辩说,我用的是“科学方法”,从头到尾,评估标准都是一致的。不过,他也诚实地表示,这项研究在我死前是完不成的,因为要见过英伦本土的每一个女人,还是有难度的。
作为科学的信徒,迦尔顿当然不满足于仅仅给各地美女排个名次。他还想搞明白,美人为什么美,美在哪里,美丽的本质何在。那时摄影术已经问世,迦尔顿便想了个办法,把各种女性的正面肖像照做成透明的,一张张叠加起来,不断增加,以此综合出一个女人的“平均相貌”。这活儿很费事,照片要用特制的纸,里面的人脸必须拍成同样的比例,他一干就是好几年,到底没得出什么有意思的结果,才告放弃。
但他始终相信,一类人一定是有共同的脸部特征的,因此在综合法之后,他又祭出了分析法。计算仍然是他最为倚仗的研究武器,比如,一个美人和一个丑人,两张肖像放在一起,只要减去他们共同的特征部分,剩下的就是区别了,这样就能看出美者为何美,丑者为何丑,人跟人到底长得有什么不一样。
迦尔顿留下的记录,告诉我们他看过不计其数的人群。他去找产科医院看一批出炉的婴儿,去找移民局观察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他去参加一个个行业聚会,对内容都不感兴趣,就为了看这个行业的人的长相。他观测过的部分人群如下:“美国科学家、浸礼会牧师、孩子、罪犯、家庭、希腊人和罗马人、利兹流亡儿童、犹太人、拿破仑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家人、肺痨病人、壮汉、博士、威斯敏斯特学校的男孩。”分类之间互有重叠,但这只能说明他是抓住一切能抓住的观察机会,过尽千帆,阅人无数。
 |
Thomas Sully所做的维多利亚女王像
不能不说这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观察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好像并不需要经过特殊的培训,但迦尔顿的严肃自律堪称表率,他坚信,要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必须搜集尽可能多的样本,活到老,搜到老。经过旷日研究,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现象:把成千上万张同类人的肖像合成起来,得出的并非所有人的平均值,相反,它比每一个个体的模样都更好看。一个好看的女人和一个不好看的女人,能合成一个更好看的女人,而不是取中间值。他跟警方说,把你们的罪犯照片都提供给我,我的研究可以帮助你们根据人的长相来鉴定他是不是不法之徒。然而,研究结果令他无法跟警方交待:合成出来的“(男性)罪犯标准像”,呃,简直一表人才。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以为的人脸之美,其实仅仅是乏味和无特色吗?或者,人要长得美,就得取消了个性吗?整容术所据的似乎就是这一逻辑。把方脸削成锥子,开双眼皮,垫直鼻梁,修尖下巴,一个标准化的美女便告下线出厂。职业时装模特必须能穿得上各种不同款式的衣服,前提条件就是消除个性,只是看脸,全长一个模样。
迦尔顿是个博物学家,人脸研究,仅是他一生工作的一部分。他去世大约八十年后,有两个美国心理学家利用电脑技术重新检验了迦尔顿的工作,证实了他的观察:人脸的“平均值”,看上去要比每个个体的长相更有魅力—间接地也证明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种总是择优繁衍……好吧,结论有点尴尬,科学家可打死都不想惹上种族主义的官司。这两个美国人赶紧作了检讨,说他们提交的论文,结论下得太武断了。
还是19世纪好,未知空间广阔而雷区寥寥,你有自由,你可以任意想象。迦尔顿爵士怎么看都像个“民科”,一辈子看了这么多美女,要我说,最有魅力的还是他自己。
作者:云也退来源一财网)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